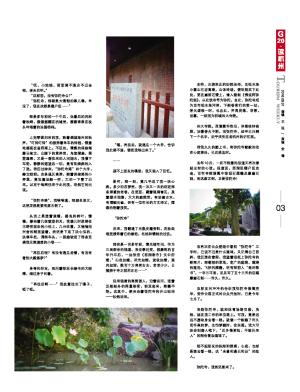|
 |
 |
“哎,小姑娘,前面路不通走不出去啦,掉头回吧。”
“这前面,没有弥陀寺么?”
“弥陀寺,那都是大清朝的事儿嘞,早没了,现在这都是棚户区……”
那是多年前的一个午后,处暑后的风和着秋蝉,微微摇颤在杭城里,窸窸窣窣在枝头吟唱着的法国梧桐。
上完琴课归来的我,聆着满城渐兴的秋声,“叮铃叮铃”的拨弄着单车的铃铛,惬意地摇逛在省府路上。不远处,清瘦的保俶塔摩云耸立,山脚下的堂弄里,鸟笼蒲扇,菜篮蔬果,又是一番往来的人间烟火,我慢下车轮,静静的遥望这一切,竟有些痴痴的入了迷。待回过神来,“弥陀寺路”四个大字,赫立眼前。这条逼仄幽深,捱着保俶路的小弄堂,竟似魔法般一样,兀的一下冒了出来。以至于每周往来于此的我,讶然它的出现。
“弥陀寺路”,我喃喃道,那顾名思义,这里定然是要有座古刹了。
头顶上是透着温暖,摇曳的树叶,慵懒,掺杂着几抹靛蓝的光,我像儿时迷路在田野里驳杂的小径上,几分欣喜,又惴惴而兴奋的朝里望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似的,扶稳车把,调转车头,一股脑驶进了那条充满我无限遐想的小巷……
“再往后呢?有没有遇见老僧,有没有看到大殿菩萨?”
身旁的好友,忽闪着那双长睫毛的大眼睛,倾过身子问着。
“再往后啊……”我故意拉长了嗓子,顿了顿。
“嗯,再往后,就遇见一个大爷,告诉我此路不通,便把我哄出来了。”
……
顾不上朋友的嗔怒,我又陷入了回忆。
是呵,那一别,竟几乎成了我一块心病。多少回在梦里,我一次又一次的迈进那条深邃的老巷,在里面,藏着琉璃青瓦,泉着碧水池塘,大大的庭院里,有岩崖古木,有蜻蜓云雀,还有一位年长的方丈师父,微微的朝着我笑。
“弥陀寺”
后来,我翻遍了无数史籍资料,在故纸堆里搜寻着它的曾经,名姓和镌刻的过往。
那还是一百多年前,清光绪年间,作为三吴都会的钱塘,虽世事迁变,然康乾的百年升平后,一如张岱《西湖香市》文中所载,”山色如蛾,花光如颊,波纹如绫,温风如酒,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
往来钱塘的商贾游人,沿着运河,连着泛船舶舟的周遭香客,纷至沓来,熙攘不绝。这其中,便夹杂着弥陀寺的开山祖师——妙然法师。
史称,云游至此的妙然法师,见松木场小霍山石岩高峻,山体玲珑,便欣然买下此处,更在崖前石壁上,请人凿刻《佛说阿弥陀经》,从此筑寺号为弥陀,自此,弥陀寺成为当年松木场河岸,下船香客们的第一站,香火盛极一时,也自此,并肩灵隐,净慈,法喜,一跃而为杭城四大寺院。
四大寺院。灵隐繁华依旧,净慈晚钟南屏,法喜香火不断,而弥陀寺,却早已只剩下一个名字,近乎消失在老杭州的记忆里。
待我久久的阖上书,将弥陀寺默默的收在心底深处,已近淡忘时。
去年10月,一则不经意的报道又再次撩起尘封的心弦。报道说,西湖区棚户区改造,百年寺院修葺中惊现石屋檐及摩崖石刻,而这座古刹,正是弥陀寺!
当再次在公众视线中看到“弥陀寺”三字时,已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记得白日西斜,我沉浸在窗前,我望着报纸上弥陀寺的新照片,那葱郁的草地,宽广的庭院,潋滟的莲池,飞拱的屋檐,还有那前人“斋沐敬书”,一字三叩首,足足写了五十三天的巨幅摩崖石刻……许久,许久。
当朋友兴冲冲的告诉我弥陀寺修葺完毕,变作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时,已是今年七月了。
虽然弥陀寺,就和体育场路交接,虽然,就在我工作的单位路上。可我,竟是迟迟不愿动身去看一眼。就像一个酝酿了许久而华美的梦,生怕梦醒时,会失落。我大可体会到唐人笔下,“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那份复杂滋味了。
经不起朋友的执拗和诱惑,心底,也却是想去看一眼,这“未曾相逢已相识”的故人。
弥陀寺,我终还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