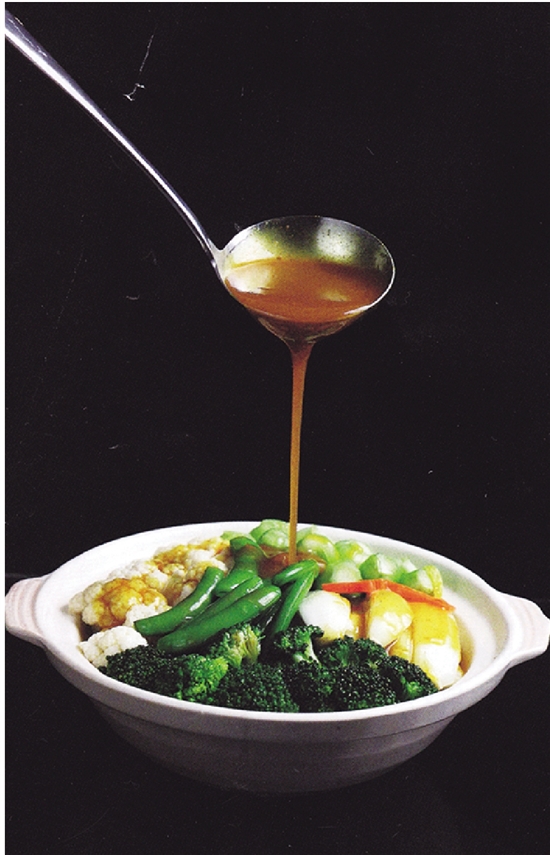 |
摩登的口味
“船规每饭必先摇铃,知会用饭。彝等一闻铃声便大吐不止,盖英国饭食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俱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馔。牛羊肉皆切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味辣且酸,一嗅即吐。”1866年,中国第一代翻译家、外交家张德彝在出访的船上,记下了自己与西餐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感受。作为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对西方的先进文明充满着艳羡,然而作为从小生活在北京的满族人,他对口味有着自己的理解。轮船上的西餐,这种难以接受的西方口味,使得张德彝形成了听见铃铛声就吐的条件反射,这大概成了他终身的伤痛。
在清代晚期,大量社会精英接触到了西餐,大家对西餐的口味评价基本相似:难吃。如近代政论家王韬认为,西餐是“既臭味之差池,亦酸咸之异嗜。”国人之味觉本是极包容的,汉唐之时的“胡味”就很快的化成了“华味”,而且对外来口味的接受往往是从精英阶层开始的,那为何西餐的味道却令张德彝们如此排斥?
因为正宗的西餐与中餐口味的差异巨大,比如西餐必备的起司(干奶酪),这口味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比臭豆腐还邪门,所以初次接触西餐的国人会有如此观感也不足为奇了。
除了初次接触的文化差异感,可能文化自负也是重要的原因。西方种种优越已然摆在了这批走出去人的眼前,科技不如人,承认就是,但是文化,我天朝上国却万万不能不如人。中国饮食文化历经千年积淀,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构成,若这也不如人,大概是不可能的吧?
但是无论张德彝、王韬他们怎么排斥,西餐的市场都在逐步扩大,并且中国人开的西餐馆也日益占领了市场。上海人的西餐馆——番菜馆有一品香、海天春、一家春、江南春等,这些名字透着中味儿的饭馆,生意如何?美食家赵珩先生说:火爆,因为吃西餐就像今天一样,是一种时髦。
美食家、中医学家、作家陈存仁在《津津有味谭》中的回忆,对此也可以佐证:“那时节(民国初年)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种风气,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看戏、坐马车,成为三部曲!”《申报》甚至认为这已构成了风气危机,挖苦那些赶时髦的学生“就是口袋里只剩下几毛车费了,也必要送到西餐馆才放得下心。”逊帝溥仪也成为了西餐的狂热粉丝,他曾在1922年创造了连续一个月吃西餐的个人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