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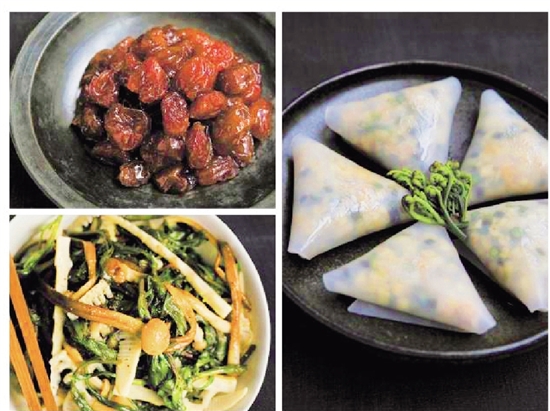 |
 |
对于江南文人而言,饮食之道兹事体大。翻看江南历史上与饮食相关的文章,便可一窥。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其中的“自然”指的是食物的品格,并非随意可得的食物,只有那些在山中自然生长的蔬类食物才算得上“渐近自然”,我们现在所说的“有机”也是达不到标准的。就我理解,这里说的“自然”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蔬菜生长的环境要不受人为的干扰和破坏,不能用人造的肥料去浇灌;二是蔬菜在生长的过程中吸收了天地的灵气。
李渔的观念包含着一种想象或者说心理体验,他认为这样生长出来的食物,更洁净,更鲜美。
“自然”是选择食物的最高标准,按照李渔的看法,生长在山林中的笋才是最为鲜美的,生长在其他地方,就没有这种鲜美之味了。而且选择了“自然”的食物,其制作之法也必须要讲究,比如笋子,它的做法颇有规范,李渔说了两个方面:其一,不能破坏它的鲜美味道,“茹斋者食笋,若以他物伴之,香油和之,则陈味夺鲜,而笋之真趣没矣”。
张岱在《四书遇》中云:“‘人莫不知饮食也’,将日用处指出道体,从舌根上拈出真味,不可做喻解。饥者易食,渴者易饮。一易字,不知瞒过多少味道矣。”饮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却不是每个人都懂得饮食之道,饮食除了满足人们的食欲外,还具有美学色彩,食物的色香味只有仔细感受才能体会出其中的微妙,而那些只是把饮食当做解决生理饥渴的人是品尝不出饮食的美味的。所以孔子说道:“人莫不知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清初的朱彝尊将饮食之人分为三种:一种是重量不重质的人,这种人只求能吃饱,并不挑肥拣瘦;一种是遍尝美味,但是由于不懂得节制,虚荣心又强,反被美食祸害了健康。在朱彝尊看来,这两种人都不懂得饮食之道,属于那种“鲜能知味也”的人;还有一种才是真正懂得饮食中“真味”的人:“饮必好水(宿水滤净),饭必好米(去砂石、谷稗,兼戒饐而餲),蔬菜鱼肉独取目前常物。务鲜,务洁,务熟,务烹饪合宜。不事珍奇,而自有真味,不穷炙,而足益精神。省珍奇烹炙之赀,而洁治水米及常蔬,调节颐养,以和于身。地神仙不当如是耶。”
由于江南一带经济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较高,所以对于饮食的要求也较之其他地区讲究。江南文人在烹饪方面都有心得,张岱、李渔、高濂、宋诩、朱彝尊等江南文人都有关于饮食方面的文字传世。
李渔在饮食方面很有心得,他在饮食中加入了很多自己独到的创意,用他的话来说是:”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渺而言之”,他独到的一个别出心裁的做饭之法,就很能体现出他的饮食理念,“尝授意小妇,预设花露一盏,俟饭之初熟而浇之,浇过稍闭,拌匀而后入腕。食者归功于谷米,诧为异种而讯之,不知其为寻常五谷也”。我也曾尝试,果真馨香可口,以一推之,龙井新上时,浇一盅龙井茶,米饭也是清香扑鼻。
李渔做鱼也很是讲究,鲜味是最重要的,其做法丝丝入扣,首先要选择合适的鱼:“食鱼者首重在鲜,次则及肥,肥而且鲜,鱼之能事毕矣。鲜宜清煮作汤;肥宜厚烹作脍。先期而食者肉生,生则不松;过期而食者肉死,死则无味”。其次,要掌握好火候,“鲜之至味又只在初熟离釜之片刻,若先烹以待,是使鱼之至美,发泄于空虚无人之境;待客至而再经火气,犹冷饭之复炊,残酒之再热,有其形而无其质矣”。再则,要注意水的分量:“煮鱼之水忌多,仅足伴鱼而止,水多一口,则鱼淡一分。司厨婢子,所利在汤,常有增而复增,以致鲜味减而又减者”。
朱彝尊的《食宪鸿秘》是一部专门谈论食物做法的论著,其中所记载的食物品种多样,做法颇多讲究,如其中记载的“肉生法”:“精肉切薄片,用酱油洗净,猛火入锅爆炒,去血水,色白为佳。取出,切细丝,加酱瓜丝、橘皮丝、砂仁、椒末沸熟,香油拌之。临食,加些醋和匀,甚美鲜。笋丝、芹菜焯熟同拌,更妙”。
高濂编撰的《饮馔服食笺》中也有不少地方是谈食物做法的,其对食物的要求也是精益求精,例如其中所说的“肉米粥”,其做法不厌其烦:“用白米先煮成,或肉汁,虾汁汤,调和清过,用熟肉碎切如豆,再加茭笋香荩,或松穰等物,细切。同饭下汤肉,一滚而起,入供。以咸菜为过,味甚佳”。陆树声认为食物之道在于其淡,不能让调料的味道喧宾夺主:“都下庖制食物,凡鹅鸭鸡豕,类用料物炮炙,气味辛浓,已失本然之味。夫五味主淡,淡则味真”。
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在饮食上似乎有一较高下的势态,写饮食的论著各有千秋,同一道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绝无重复。
江南文人由于注重饮食,曾传出过不少佳话,据《丹午笔记》载,“万历年间,南院俞君宣琬纶,幼孤。甫操觚,母遍访名师。闻有名士某善啖者,延之,闻俞文,谓俞母曰:‘汝家计若干,’母以实告。师曰:‘可供二年半餐馆,汝子学亦成矣。’师不受束脩,但求果腹,如猪肚中肝肠肚脏等物,只供得点心一餐。既而期满辞别,俞家计亦索。师谓君宣曰:‘承令慈厚德,何以为报。’即命做‘何以报德’题文,竟成佳作”。这让江南一带的饮食增添了许多文化的气息。
当然,食物除了做得好,还需要有懂得食物的人来品尝。品尝美食不只是大快朵颐,同时也是建构有意味的生活。
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常常对某种食物有特别的嗜好,因而在品尝所嗜好的食物方面煞费心机。
李渔嗜吃蟹,为吃到美味可口的蟹,到了痴狂的地步,他每年都会在蟹上市之前筹备一些钱用于买蟹,李渔称之为”卖命钱”,凡是与蟹有关的物品都被其特别命名:如糟名”蟹糟”,酒名”蟹酿”,翁名”蟹瓮”,甚至家中要雇一个特别会做蟹的佣人,将其取名为”蟹奴”。由于不能尽兴地吃蟹,李渔还感慨有负于螃蟹。
张岱也是喜欢吃蟹的人,在回顾前事的时候,他特别写到了当年和兄弟友人一起吃蟹的情景,“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瓜以谢橘、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蟹会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聚餐,而是融汇在张岱的情感之中,“由今思之,真如天厨仙供”。这后来成为他追忆昔日繁华生活的一种依托。
饮食之道,很多时候传递的是生活之道,“好好”吃饭何尝不是“好好”生活呢。不如,今日就学文人“好好”吃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