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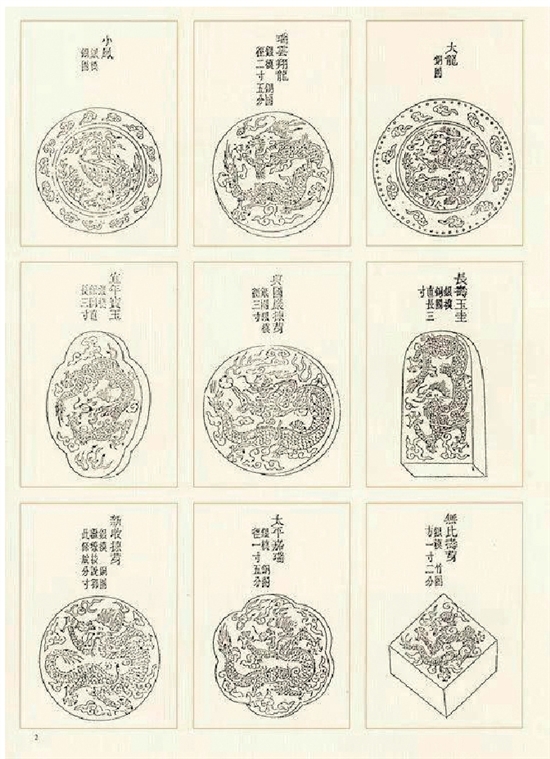 |
 |
宋代茶生活的雅致追求,在宋代遗留下来的文字和画作中可见一斑。
苏东坡曾写下一首诗:“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流连。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可以想象的出,900年前,他来到惠山的天下第二泉,拿出他珍贵的小龙团茶,名泉配名茶,想来他一定品的欣欣然,陶陶然。
小龙团是宋代茶文化中的闪烁的明星,而说到它就不能不提起另一位文人,同样是书法家的蔡襄,他与苏轼、黄庭坚和米芾并称“宋四家”,而这位蔡襄同时也是宋代的一大茶人,他是小龙团茶的创制者。
蔡襄在宋代茶史中的独特地位,一如唐朝的陆羽,后世流传了很多他与茶有关的趣闻轶事:
在建安能仁院有茶从石缝里生长出来,于是寺里的僧人就采来制造了八饼茶,起名字叫石岩白,然后将其中的四饼送给了蔡襄,剩下的四饼茶派人带到京城送给了王禹玉,然而蔡襄并不知道除了自己之外还另有四饼茶,过了一些日子,蔡襄被召回京,有一天他去拜访王禹玉,主人就让家人在自家的茶笥里挑选精品茶招待蔡襄,当茶奉上来的时候,还没等品尝,蔡襄就捧着茶瓯对主人说:您的这个茶极像建安能仁院里的石岩白,您何从得之?王禹玉很是惊讶,怎么蔡襄不用品,一看就能知道是什么茶,于是将信将疑的让人拿来茶的标签,一验证果然不错,正是石岩白!
如此辨别茶的能力真是神乎其技。
据欧阳修的《归田录》记载:蔡襄制作的小龙团茶,一斤要卖二两黄金。即便如此,也是金可有而茶不可得,由此可见小龙团茶在当时之珍贵。难怪苏东坡烹小龙团会如此之得意了。苏东坡的嗜茶也是有名的。在他留下来的诗作里,与茶相关的便有很多。
除此,苏东坡对茶还有独到的见解,《续茶经》辑录的文献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光有一次与苏轼论茶,他说茶和墨有着截然相反的品质:茶越白越好(宋代茶色贵白),而墨则越黑越好,茶是重的好,墨是轻的佳,茶要喝新的,墨却要用陈的。苏轼听了却不以为然,他另辟蹊径:“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抛开外在形制,直接讨论其内在品质,在找出茶墨二者共性的同时上升到品德与操守的道德层面,实在精彩。
再说到饮茶,“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之争箧笥,争鉴裁之妙。”两宋时期的饮茶方式主要为煎茶法和点茶法,而点茶法更是成为宋代茶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宋代皇室和士大夫的参与,更是将品茶艺术推至登峰造极之境。
这次展览中“烹点之妙”单元通过大量文物展示,完整体现了宋代饮茶全貌。
如今流行日本的抹茶便是点茶的演化。“点茶”技艺,炉火纯青便可称为“分茶”,北宋《清异录》中记述: “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 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幻灭”,可谓出神入化。
展馆里的茶碗仿佛还残留着点茶时的馨香。点茶时用的茶盏多是斗笠状,在点茶时,先用瓶煎水,然后将研细茶末放入茶盏,放入少许沸水,先调成膏。所谓调膏,就是视茶盏大小,用勺挑上一定量的茶末放入茶盏,再注入瓶中沸水,将茶末调成浓膏状。接着一手点茶,通常用的是执壶往茶盏点水。点水时,要有节制,落水点要准,不能破坏茶面。与此同时,还要将另一只手用茶筅旋转打击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称之为 “击拂”。如今这些器物都安静的躺在玻璃柜里,只有表层的包浆和沁色记录着过往的岁月,也让我们一窥那盛世清尚。
宋代文人雅士亦喜斗茶,所谓斗茶,主要“斗色斗浮”, 色是指茶汤的颜色,而浮是指茶沫咬盏的时间。想着宋人斗茶时,小小杯中“乳雾汹涌,溢盏而起”,该是何等清趣闲雅。
展馆中还悬挂着一些宋代的画作。在这条宋画之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宋时蜡烛摇曳的微光,桌案之上竞相绽放的插花,以及“瑞脑销金兽”的香炉, 以及宋人分茶时那杯中绽放的清雅。宋时的家具也着实令人喜欢。床与塌、案与桌、椅与凳、屏风、台、架、几,都是那么简洁而有韵致。宋式的审美风格,是宋朝文人闲适、优雅生活的折射,不饰奢华,坦荡独立。
只是,千古兴亡,朝代更迭,多少往事,都付笑谈!经历元朝游牧民族的统治,再经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粗放式习惯引领,那些曾经精致优雅的社会风俗,便被引领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茶艺如此,其他的生活习俗亦如此,曾在《风雅宋 : 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一书中,就读到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一个如此精致、优雅的宋朝就这样泯灭于时空之中。时光转瞬千年, 那个风雅的宋如今只能在故纸堆或者像今日这般的展览中去找寻,并还原那个被陈寅恪先生鉴定为“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