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与文化不是拔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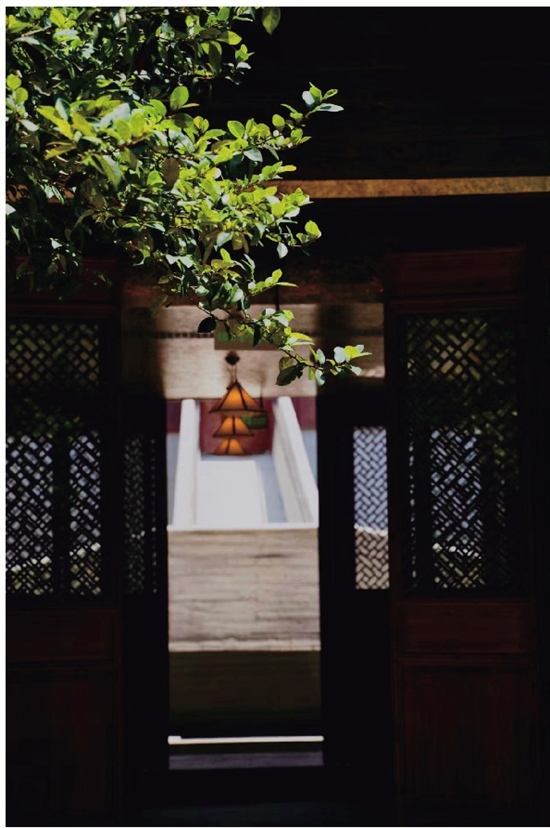 |
 |
 |
 |
提到藏书楼,很多人会想到各种老建筑。事实上藏书楼只是一个古代藏书处所的泛指,只要有藏书作用的都可以称其为藏书楼。
在我国各地散落着很多这样的藏书楼,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当下,随着文化消费水涨船高,依托文化资源,完善城市经济发展结构,成为推动城市更新及发展的重要手段。“藏书楼”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延展了城市的文化记忆,拥有了新的文化力量。
商业与文化不是拔河
◎ 记者 王 珏
2022年7月23日,宁波市政府重启抱珠楼。抱珠楼是清道光年间浙东著名的藏书楼,为冯骥才高祖的从弟冯本怀所创办。2007年,浙江图书馆在其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将抱珠楼和天一阁一起列入浙江省存世的十四座著名藏书楼之中。自此,慈城冯氏抱珠楼,与宁波天一阁、余姚五桂楼并列为宁波三大藏书楼。
盘活闲置的文化资产,延展城市的文化记忆,可以更好的推进慈城古城的建设。如何改造这座建筑,使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宁波市政府提出利用原有建筑的空间特性,将之改造成一座优秀传统与创新思维相融合的新式藏书楼。于是,当隐居集团的创始人黄严提出“天下读书人共建藏书楼”时,双方一拍即合。
这个“合”来自于两个思路,一个是让更多爱书的藏家,有存书的空间,以及让沉睡于民间的藏书,重新进入社会,发挥价值。另一个是提出了共享的概念,最大化发挥民间藏书,传承传播人类文明文化载体的价值。
于是,这座藏书楼由政府提供公共空间,邀请具有创新意识的专业团队设计,委托社会机构运营,让沉睡于民间的个人藏书重新进入社会流通,激发藏书背后隐藏的人文价值,让藏书楼有了新的时代价值。。
这个文化活力依托于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空间”这个概念涵盖了“公共的”空间,“文化的”空间,“公共文化的”空间,三个层面的内涵。这包含了文化设施,文化场所和文化活动,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想起老舍先生曾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由此可见公共文化空间的流变,是社会变革的晴雨表。
从乡里社会跨越到现代社会,慈城古镇抱珠楼的属性,从原住民日常生活的场所转变为提供给旅游者体验消费的场景,其运营方式也从基于乡规民约的自治,转变为文化旅游发展中“一中心多主体”的共治。因此我们可以在遗产保护、旅游开发、地方发展、文化消费等复杂语境下探讨慈城古镇抱珠楼文化空间的生长问题。
毋庸置疑,书是这座藏书楼的主角。抱珠楼将书放在对人来说最重要最舒服的位置,不仅仅希望把书作为一个符号,让人去观赏这些书,更是希望人能融入进去,以人的活动丰富书的内容。让同样喜欢阅读,喜欢藏书的人聚集到这里,它既是物理的聚集空间,也是精神的凝聚场所。
从藏书楼回归到文化公共空间这个话题。一个地方的公共文化空间,对于原有的居民而言,是日常的,真实的,饱含回忆的。而当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地理边界和群体边界逐渐被打破,这就需要我们的公共文化空间更加的多元。这就需要公共文化空间延展出能够满足旅游者对于异文化的想象和找寻。作为“被凝视的景观”,公共文化空间不仅仅成为旅游者进行在地性文化体验和旅游消费的对象,还应成为承载旅游者消费活动的场所。
面对文化功能的延展和运营方式的改变,政府职能以及与市场的合作方式必然要发生改变。“公共文化空间的开发必须遵循文化至上的逻辑,容不得商业的侵蚀。”这是一种声音;“纯文化的东西难以盈利,只有商业化开发才能长远发展。”这是另外一种声音。
在这两种观念的冲突之下,产生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与隔阂。然而,公共文化空间的治理是一个多元复杂的问题,如果仅仅将商业与文化看作二元对立的关系,就不能解决其中更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空间运营获取盈利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才是抑制或者加速增长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黄严说。
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保护和商业开发贯穿抱珠楼的整体运营方案。对于公共文化空间这样一个特殊的治理对象,既要把它当作是慈城古城这一特殊场域里具有商业属性的文化资本,对其进行商业化运营;也要把它当作是用于稀释浓厚商业氛围的公共文化设施,对其进行事业性运作。商业和文化的观念冲突,不是二者选一的问题,而是商业多一点还是文化多一点的平衡发展问题。
文化旅游发展中的慈城古城,是文旅产业化与地方性视阈下“文化变迁”与“多元治理”问题的缩影,折射了旅游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权力、民生等复杂问题的交互作用。由于抱珠楼兼具多重身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在复杂语境下探讨公共文化空间治理机制的构建,不仅对慈城古城意义深远,还将为其他类似城市中藏书楼的运营发展实践提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