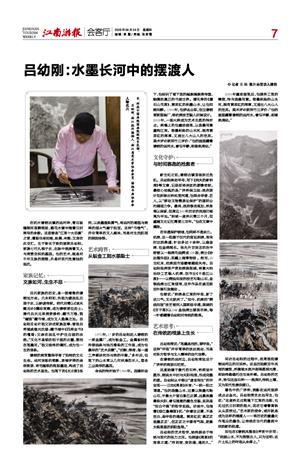吕幼刚:水墨长河中的摆渡人
吕幼刚:水墨长河中的摆渡人
◎ 记者 王 珏 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人物名片:
吕幼刚,浙江杭州塘栖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塘栖书画协会会长,师承中国画院国画院副院长范扬。
在杭州塘栖古镇的运河畔,青石板缝隙间苔藓斑驳,雕花木窗半掩着旧时商号的余韵。这里曾是“江南十大名镇”之首,漕船往来如梭,丝绸、米粮、文房在此交汇。生于斯长于斯的画家吕幼刚,家族七代扎根于此,血脉中流淌着文人与商贾交织的基因。他的艺术,既是对千年文脉的致敬,亦是对现代性侵蚀的抵抗。
家族记忆:
文脉如河,生生不息
吕氏家族的历史,是一部缩微的塘栖地方志。元末明初,先祖为避战乱迁居于此,以耕读传家。明代吕需以《谈天雕龙论》震动南雍,成为塘栖首位进士;清代吕氏兄弟捐资修桥、藏书万卷,筑“樾馆”藏书楼,成为文人雅集之地。吕幼刚自幼听祖父讲述家族故事:曾祖吕希随戚继光抗倭;藏书楼中《四库全书》的檀香;父亲在战乱中护住古画的决绝。“文化不是锁在柜子里的古董,要活在笔墨间。”祖父临终的嘱托,成为他一生的信条。
塘栖的商贸繁荣孕育了独特的文化生态。运河货船的剪影、茶楼评弹的吴侬软语、老宅楹联的斑驳墨迹,构成了吕幼刚的艺术底色。他笔下的《水北街》系列,以淡墨渲染雾气,将运河的潮湿与商埠的烟火气凝于纸面。这种“书卷气”,并非简单的文人趣味,而是对生活肌理的深刻体悟。
艺术跨界:
从钣金工到水墨隐士
1972年,17岁的吕幼刚进入塘栖的一家金属厂,成为钣金工。金属板材的冷硬线条与油污浸染的工作服,成为他最早的“艺术启蒙”。“切割、焊接,每一道工序都讲究形与势的平衡。”多年后,他笔下的山水常以几何状峰峦示人,隐含工业美学的基因。
命运的转折始于1983年。因缘际会下,他结识了被下放的越剧编剧周传国,触摸到真正的书画世界。潘天寿的《鹰石山花图》、黄宾虹的积墨山水,让他如痴如醉。1990年,他辞去公职,创立塘栖首家服装厂,将杭绣技艺融入时装设计。
2003年,一场大病成为艺术生涯的转折点。病榻上的他重拾画笔,以泼墨写意重构江南。宿墨积染的山水间,既有黄宾虹的浑厚,又透出八大山人的空灵。美术评论家郑竹三评价:“他的画里藏着塘栖的运河水,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
文化守护:
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者
新世纪之初,塘栖古镇面临拆迁危机。吕幼刚奔走呼号,写下《消失的新桥湾》等文章,记录即将消逝的廊檐老街。最惊心动魄的是广济桥保卫战:政府原计划拆除古桥拓宽河道,他联合学者、匠人,以“移动文物需原址保护”的国际公约据理力争。最终,政府修改规划,桥身得以保留,但周边300年历史的民居仍被夷为平地。“拆掉一座桥只需三个月,但重建文化记忆需要三百年。”他在文章中痛陈。
在非遗保护领域,他同样不遗余力。
杭绣,这一起源于汉代的宫廷刺绣,南宋时达到鼎盛,针法多达十余种,以盎金绣、包金绣闻名。张允升百货店的孙仲舒曾以一根绣花线劈成128股,绣出《妙法莲华经》,现藏上海博物馆 。然而,20世纪末,杭绣因市场萎缩濒临失传。吕幼刚抵押房产资助绣娘陈娟,将意大利抽纱工艺融入杭绣,创作出《千里江山图》——以劈线如发的技艺勾勒山石,金银线绣出江南烟雨,这件作品在威尼斯双年展引发轰动 。
他曾说:“刺绣是江南的呼吸,断了这口气,文化就死了。”如今,杭绣的“劈线如发”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陈娟的《百子图》以24K金线绣出婴孩衣袂,每一针都藏着吕幼刚对传统的敬畏。
艺术思考:
在传统的根脉上生长
吕幼刚常说:“笔墨是活的,要呼吸。”这种“呼吸”并非简单的技法流动,而是对东方哲学与文人精神的当代诠释。
在塘栖的运河边,吕幼刚常驻足于广济桥的斑驳石栏前。
这座始建于唐代的石桥,桥洞呈半圆形,倒映水中时与天际相接,形成完整的圆。吕幼刚从中悟出“虚实相生”的宇宙观——正如《周易》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他的泼墨山水,近景以焦墨勾勒山石,中景大片留白象征云雾,远景淡墨晕染天际,看似随意的墨色交融,实则是“知白守黑”的哲学实践。访谈中,他指着《烟江叠嶂图》说:“你看这云雾,不是空白,是呼吸的通道。黄宾虹说‘黑团团里墨团团’,但团团之中要有气眼,就像太极图里的阴阳鱼眼。”
吕幼刚的艺术哲学,始终游走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之间。他深谙《周易》的变易之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2003年重拾画笔后,他摒弃工笔的精致,转向泼墨写意。宿墨积染的山水间,既有黄宾虹的浑厚,又透出八大山人的空灵。美术评论家郑竹三评价:“他的画里藏着塘栖的运河水,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
采访吕幼刚的过程中,我常想起塘栖运河边的石拱桥。这些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建筑,桥墩被水流冲刷得圆润光滑,却始终稳稳托住往来舟楫。吕幼刚的艺术,恰似这些石桥——既深扎传统土壤,又为现代性提供渡口。
暮色中的广济桥,倒影在运河里碎成点点金光。吕幼刚常在此处写生,他说:“这座桥见过乾隆下江南的龙船,也见过抗日时期的炮火,现在它看着高铁从头顶掠过。”艺术家的使命,或许就是成为这样的摆渡人——将历史的重量化作笔尖的墨色,让传统在当代的激流中找到新的航道。
如他在《塘栖风雅录》序言中所写:“我画山水,不为致敬古人,只为证明:这片土地上的呼吸从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