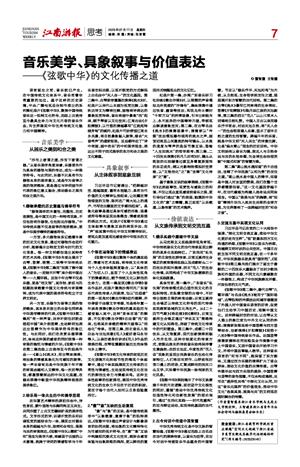音乐美学、具象叙事与价值表达
——《弦歌中华》的文化传播之道
音乐美学、具象叙事与价值表达
——《弦歌中华》的文化传播之道
◎ 董智慧 王智媛
语言诞生之前,音乐就已产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音乐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基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推出的系列微纪录片《弦歌中华》,聚焦中国传统音乐这一独特文化符号,选取上古流传至今最具生命力与文化内容的音乐作品,向世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和中国精神。
音乐美学
从器乐之美到和合之美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音乐美学角度来看,乐器首先作为具体的器物与美的传达,成为一种美学符号。与此同时,乐器不只具有作为器物本身的美学意义,或是作为音律之美的物质载体,更是通过与诗词画作所代表的象征意义融合,推动器乐之美向和合之美升华。
1.器物承载的历史意蕴与美学符号
“器物美学的丰富性、完整性、历史连续性,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不仅包括有形器物,也包括无形器物。”中华传统乐器不仅是音律的物质载体,更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凝练符号。
一方面,多元器物体系记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对器物形态进行分析,能够揭示出特定文明与时代的文化信息。每一种文明都创造出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弦歌中华》向受众展示了古琴、笛箫、琵琶、二胡等中华传统乐器。《弦歌中华》第二集用“如果了解中国人的音乐,一定绕不开琴”来介绍中国古琴——九霄环佩。这张千年古琴不仅是乐器,更是“活文物”,其形制、断纹与苏轼题刻承载着中国文化传统与审美精神,成为代表中国的美学符号屹立于世界文明史。
另一方面,乐器作为音律之美的物质载体,其本身所发出的乐音也同样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代表。《弦歌中华》第二集用“有一种声音,当你听到他时就会想起中国”来介绍笛箫,生动鲜明地表达出笛箫作为中华美学符号的象征性。与此同时,我们在欣赏乐器弹奏时,体味这种美的感受的同时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与情感的升华。《弦歌中华》在第二集选取上古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高山》《流水》,用古琴来演绎,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为可感知的旋律,每一声乐音背后是中华民族千年不衰的审美志趣和人文精神,每一次抚琴弄弦,都激荡着深远的中华文化底蕴,在器乐弹奏中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思想的美学象征。
2.诗乐画一体共生的中和美学呈现
在华夏艺术精神的原初形态中,诗性言说、素朴造物与乐舞同构互文共生,共同形塑了上古文艺肇始阶段的美学范式。文字形式的诗、诉诸听觉的乐和诉诸视觉的画结合为一体,展现出对器乐本身的超越与升华,发挥和合相生、美美与共的审美效应。《弦歌中华》以儒家“中和”理念为美学内核,将凝固于古画的山水意境、流淌于诗词的情感哲学与千年乐音交织共振,以视听联觉的方式解码上古名曲中“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第二集中,古琴家李蓬蓬在演绎《流水》时,纪录片以宋代山水画为视觉注解,以春秋古诗文为精神注解,画卷将诗表达的景象视觉转译,音乐将画中景象“活”起来,赋予琴音以文化空间;江南古曲《夕阳箫鼓》,以竹笛的清越摹写“江流宛转绕芳甸”的婉约,纪录片巧妙穿插江南水乡风景,将自然景象融入旋律,暗合“大音希声”的道家哲思。这些都呼应了“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中和美学理念,表达出不同于西式美学的东方和合之美的文化意蕴。
具象叙事
从主体叙事到意象互映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具象化叙事是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场景或符号等来呈现抽象概念、情感或思想的表达方式。纪录片《弦歌中华》通过主体叙事与意象互映的表现手法,在“声”临其境中活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使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华弦乐的文化魅力。
1.个体在场体验下的情感表达
《弦歌中华》通过聚焦个体的真实经历、情感与艺术实践,将传统文化传承与个人生命体验深度融合,以“具体的人”为切入口,呈现了个人主体性视角下的情感表达,赋予传统文化以鲜活的生命力。在第一集呈现《赛龙夺锦》音乐作品时,纪录片聚焦沙湾何氏广东音乐代表性传承人何滋浦,他以“注经者”的第一视角对《赛龙夺锦》进行阐释,并非停留于曲谱文字考据,而是将年复一年亲身演奏《赛龙夺锦》的真实经历与感受融入其中,这种“身体在场”的解读,不仅使《赛龙夺锦》古曲谱“活”起来,也将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得以“活态化”传承。在第三集,西北音乐人张尕怂与当地民歌《花儿》爱好者马永华等人,以亲历者身份讲述《花儿》作品的演绎历程,在琴弦震颤间融注生活体悟与乡土情怀。
《弦歌中华》将文化传承的宏观历史文化语境内化到细节性的微观个体叙事中,通过个体实践展现文化传承的日常性与情感性,生动呈现传统文化在当代的鲜活生命力与情感共鸣。这种主体性叙事的创新路径,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历史的积淀,更在于每个当代人如何以自身经验激活它。
2.“意”“象”互映的生动复现
“意”与“象”的互映,是中国传统美学中“以象载意、意寓于象”的独特表达。《弦歌中华》通过声音设计与影像语言的协同共振,将抽象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视听符号,在“意”“象”互映中构建起沉浸式文化空间,既弥合感官体验与抽象思维的鸿沟,更以鲜活的复现形式唤醒观众的文化记忆。
纪录片第一集,沙湾广东音乐研习社排练《赛龙夺锦》时,以琵琶的声音模拟龙舟竞渡的“冲锋号”,集体演奏中通过快音、重音等技法,再现龙舟比赛时“千军万马”的拼搏场景,引申出积极向上、永不放弃的中国精神内涵,带领观众解读意象空间;第二集,在古琴名曲《流水》的演奏场景中,演奏家以“吟猱”技法模拟瀑布倾泻的流水之声,画面切换至山间激流的特写镜头,以水流的速度与琴声的急促节奏互映,隐喻“人生如流水”的哲学思考;第三集,二十四伎乐演奏《明月几时有》时,镜头从斑驳的石刻缓慢过渡至身着复原服饰的乐团成员,辅以光影特效模拟时空穿梭,以“文物活化”之“象”诠释“文化传承”之“意”。
基于意象互映的叙事策略,《弦歌中华》达到叙事性、观赏性与感染力的和谐,不仅让观众直观感受到音乐之美,更引导他们透过“象”的表层,触摸到中华文化的“意”之精髓,真正实现“以乐载道,以象传意”的艺术境界。
价值表达
从文脉传承到文明交流互鉴
1.器乐实践中赓续中华文脉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视角审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当代传承呈现出鲜明的具身化实践特征。广东民间“私伙局”的自发性社群传承、云南玉溪师生合唱团的教育浸润实践以及成都街头二十四伎乐的即兴展演、西北“花儿”的生态化传唱,共同构成了中华文脉赓续的立体化实践图景。
具体而言,第一集中,广东音乐“私伙局”的传承模式则凸显市民文化的自组织特性,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中,不时传出悠然自得的岭南曲韵;云南玉溪师生合唱团以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实现教育场域的文化再生产。从《二十四节气歌》《将进酒》到《清明》,云南玉溪师生合唱团通过“诗乐互文”策略构建文化认知路径,突破了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代际壁垒。第三集中,成都二十四伎乐,从文物复原、现代创新演绎到融入市井生活,这种非制度化的传承方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音乐始终保持着生意盎然;在西北地区,年度性的“花儿会”现象则呈现出民族音乐的生态化传承特征,人们将田间劳作、山野放牧时信口漫上的词语,汇聚成鲜活的民间口头文学,闪烁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讯息。
《弦歌中华》深刻揭示了中华文脉赓续千年的内在逻辑,即在坚守文化根性的同时,遵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指引,通过“生活化实践——时代性重构”的双向辩证运动,实现传统基因的当代激活。
2.古今对话中传递中国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脉的智慧结晶,《弦歌中华》通过选取上古名曲在当代的演绎传承,以音乐为纽带,在古今对话中传递弦乐作品蕴含的中国智慧。节目以“器乐抒怀、天地和鸣”为内核,从自然观、生命哲学到交往之道,层层展开东方智慧的当代回响。第二集的古琴《流水》摹写江河奔涌的生命律动,笛箫《夕阳箫鼓》勾勒月映江波的天地韵律,第三集的西北“花儿”以山川草木入词唱响自然礼赞。中国人自古以来用器乐抒怀言志,对话天地自然,将“天人合一”的生态哲思谱入乐章,显示了顺乎自然之道的生活智慧。跨越千年的乐音,既是中华文明“天人共生”的诗意注脚,也是“绿水青山”理念的历史回响。中华文明始终以音乐为镜,照见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永恒命题,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式和谐”的智慧方案。
第二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诠释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交往之道。“高山流水是中国人的情怀,知音是中国人对友谊的赞美,我们在整个世界都需要知音。”这一文化基因穿越千年,在当代凝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以“美美与共”的胸襟,将“知音”精神升华为人类共生共荣的全球方案,为世界奏响了一曲跨越时空的“和合之音”。
3.交流互鉴中实现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弦”就像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弦歌中华》以弦乐为桥梁,构建跨文明对话的公共空间。中国自古就主张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在一千多年前,中华民族器乐就具有“国际范”。《弦歌中华》第三集向我们展示了诞生于唐朝的二十四伎乐大量融合了当时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器,不同文化元素凝聚在一件器物上,构成了中华民族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
《弦歌中华》第二集中,唐代古琴“九霄环佩”与名曲《流水》被用于“国际场域”,古琴独特的吟猱技法和减字谱激发了外国人对中国音乐语言的好奇,促使他们主动学习中国历史、理解中国文化。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古琴从文人雅士的象征变为中外文化认同的桥梁;演奏家张维良将中国笛箫与西方竖琴结合,创新演绎《夕阳箫鼓》《胡笳十八拍》等中国传统音乐作品。法国竖琴演奏家赛琳在同张维良合作演奏中爱上中国音乐,又因中国音乐开始学习中文,并将中国故事融入教学。这种音乐语言的“和而不同”,既保留了东方韵味,又通过西方乐器的演绎扩大了受众群体,推动文化价值的共情传递。古琴吟猱手法与西方乐理的差异、中国笛箫与竖琴的音色碰撞,不仅未构成隔阂,反而在“差异性共鸣”中深化文化认同,印证“音乐无国界”的价值理念,推动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在国际舞台的传播。
(作者董智慧系浙江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王智媛系浙江省青年书法协会诗词与楹联委员会秘书长)
资金资助: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空间正义视域下浙江省城乡美育失衡及其数字化治理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SB149)